中印要“对话”,不要“猜疑”

1991年秋天,刚从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硕士毕业的年轻学者狄伯杰从香港转机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生涯。学习期间,他还与同在北大学习的中国姑娘王瑶相识相恋,数年后喜结连理。
那时的中国内地和印度之间没通直航,来中国留学的印度学生寥寥无几,中印之间的跨国婚姻更是少之又少。但到今天,人们可以从国内多个城市直接飞抵对方国家,来中国留学的印度学生数量超过13000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组建的家庭也屡见不鲜。
后来回到尼赫鲁大学继续学术研究的狄伯杰如今已经成为印度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和中印关系学者。在他看来,虽然当下的中印交往在两国国际交往大数据中占比还很小,但与26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日,在狄伯杰教授访问北京期间,本刊记者就中印关系和文化交流等话题与他进行了对谈。狄伯杰用汉语接受采访,完全不回避中印之间存在的新旧问题,但他通晓中国文化,对中国人乃至中国对外交往的“性格”有深入理解,他认为推动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解药在于“对话”,而非“猜疑”。

印度著名汉学家狄伯杰认为,在印度传播中国古典文化有助于印度人更好地理解中国。图为狄伯杰在游览中国长城。
“一带一路”可否延伸到印度?
2016年11月5日,狄伯杰在印度北阿坎德邦的都安大学进行了一次讲座,给师生们专题介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位于印度东北部的北阿坎德邦与中国西藏接壤,属于“一带一路”西向联通的关联区域。作为都安大学中文系的创建者,狄伯杰希望更多的印度普通人和年轻人能了解中国和“一带一路”的具体情况,因为“除了知识界人士,印度人对‘一带一路’几乎没有概念”。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于2013年,其核心在于发挥中国交通建设的优势,通过基础设施联通,推动中国和周边国家进行深入的发展对接,进而将“增长的亚洲”和“发达的欧洲”连接起来,带动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
三年多时间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示支持,4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不过,这个名单中并不包括中国西南方最大的邻国印度。据狄伯杰分析,印度不积极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少人认为“中国对于印度的敏感问题不敏感”:不仅“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之一中巴经济走廊涉及印巴领土争议,活跃在东北邦地区的一些武装反对派也是印度很大的安全顾虑,在这些地区与中国合作自然是困难重重。但狄伯杰并不认可印度官方当前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他认为漠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顾虑”。“正是因为有问题,才需要谈判。印度应该和中国以及巴基斯坦共同讨论合作,看是否有可能把中国西部联通的某些走廊支线延伸到印度境内,以此推动三方互信。”
狄伯杰举例说,如果中巴经济走廊的某些地段延伸到印度西部,甚至古吉拉特邦,那么就可能从中推动印度和巴基斯坦建立信任措施。在能源合作方面,虽然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项目已于2015年底正式启动,但线路长,过境区域形势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是不是可以和中国商谈一个新的经济走廊,把新疆和中亚的联通优势继续伸到印度北部,比如说达拉克地区。边界分歧可以搁置和管控,不应影响双方基建和经济合作交流。”
再比如,根据“一带一路”南线铁路联通规划,从中国西藏日喀则通往中尼边境的铁路正在修建中,预计可于2020年完工,之后铁路还将修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和其他城市。“印度边界地区是最穷的地方,如果中印铁路网能在中尼铁路的基础上实现对接,既可以让当地人得利,又可以缓解安全威胁,促进经济合作,三方都受益,为什么不能做呢?”
印度舆论常常认为,和中国合作就会带来安全挑战,但狄伯杰觉得“印度需要解放思想,要改变思维和心态,通过对话、联通和交流来去掉对中国的心理恐惧。猜疑只会让状况更加糟糕”。

上世纪90年代初,狄伯杰在北京大学访学期间,结识了中国姑娘王瑶,数年后二人结为夫妻。
“印度需要中国”
去年4月,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在即,瑞士知名国际关系学者让·皮埃尔·拉赫曼发表观点说,西方国家不可能强迫中国去遵守自己都不遵守的规则。“如果人们对中国的崛起依旧置若罔闻的话,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所谓的‘新兴经济体’,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金砖国家,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全球性的超级大国。而且,中国还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依靠侵略他国而崛起的世界大国。”
这也是狄伯杰眼中正在深刻影响中印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崛起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和权力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印度要看清楚这个现实。印度不少学者一方面羡慕中国的发展成就,比如在短短几十年里减少7亿多贫困人口,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实力心怀恐惧。印度非常关注中国大量的国防投入,但这与中国的经济奇迹有关,如果印度的整体经济水平提高,同样会给国防投入大量财力。”
从去年年初以来,因为在反恐和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等问题上分歧不断,再加上“一带一路”、边界争议和达赖等新老问题,中印关系一路下滑,以至于去年年底的排灯节期间,印度社交媒体发起了“抵制中国货”运动。狄伯杰认为,这些事件其实都是莫迪政府与印度人民党推崇民族主义路线的反映,这也正是影响中印关系的第二大因素。
“莫迪政府过于走民族主义的路线,用一些小的争端来造成僵局,这不是明智的决策,不应该因为这些问题绑架整个中印关系。反恐不是中印之间的主要问题,加入核供应国也不是,主要问题是我们要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双边关系,同时要看全球政治权力结构变化。狭隘的视角不仅不会给两国方带来好处,还会在很多方面破坏中印关系,加深互不信任的状态。”
不过,虽然当前的中印关系波折颇多,但两国经济发展战略却有诸多契合点,不仅印度国内区域联通规划有可能和“一带一路”连接,中国经济转型也正赶上了“印度制造”战略,经贸领域的合作前景被广泛看好。目前,有超过500家中国公司在印度注册,印度已成为中国对主要经济体投资增速最快的国家,中国去年对印度的投资高达10.63亿美元,是2015年的6倍多。“虽然印度没有公开表态要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但莫迪政府在务实合作方面很明智,双方领导人互访签署的协议里已经包括两国企业要展开的合作。”
狄伯杰提到两个数字:在能源领域,尤其是电力方面,中印企业合作非常紧密,印度约有80%左右的电力设备都来自中国,诸如信实工业等大企业莫不是靠着中国公司起家;此外,印度作为“世界药房”而享誉全球,而印度药品之所以廉价,是因为90%的原材料都来自中国。如果中国禁止原材料出口印度,其制药业会受很大打击。“中国在印度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虽然双方贸易总额还不尽如人意,但已经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如果中印能够在各自的经济和国家发展方面有更好的合作,对接发展战略,效果会更好。”
就在今年3月初,印度辩喜基金会的部分学者与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学者就未来美印关系进行了探讨,其中有关加强印美日合作的声音引起外界关注。在狄伯杰看来,中国和印度在安全方面可能会渐行渐远,印度确实是在靠近美国、拉拢日本,“但印度也肯定不会成为美国的副手,因为印度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国,希望在国际事务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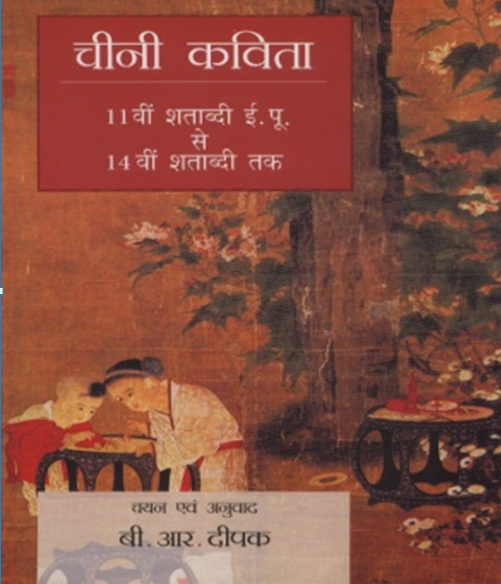
“认识中国不能少了文学”
塞兰坡是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市所辖的一个小镇,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地名都极其陌生。但在1809年,最早的中国儒学经典英译本就出现在这里,译者为英国传教士马士曼,他翻译出版了《论语》前九章。13年以后,1822年,这位传教士又在这里出版了最早的《圣经》汉译全译本。
狄伯杰在研究中印学过程中注意到了这段历史。据他介绍,早在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印度就已经开始培养汉语人才,但因为学生不多,后来没有持续下去。1921年,印度学者泰戈尔在圣迪尼克坦小镇上建立国际大学,并先后聘请了多位汉学家传播中国文化。曾被印度总理英吉拉·甘地称为“伟大学者”的谭云山是其中的先驱人物,他不仅创办了《中印研究》,还于1937年靠个人力量筹建了国际大学的中国院,现在学校里的许多旧图书都还是他在民国时期从大陆带去的。
但狄伯杰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虽然将近200年前印度就出现了重要的中文译作和典籍,也曾有老一辈学者倾力推动中印文明文化交流,但近几十年来印度在培养汉语人才和翻译汉语作品方面的成效却“令人失望”,中印在高校合作、媒体对话或旅游互动等多方面都欠缺对话机制,而语言不通和交流不畅直接影响着中印互信对话与经贸领域的深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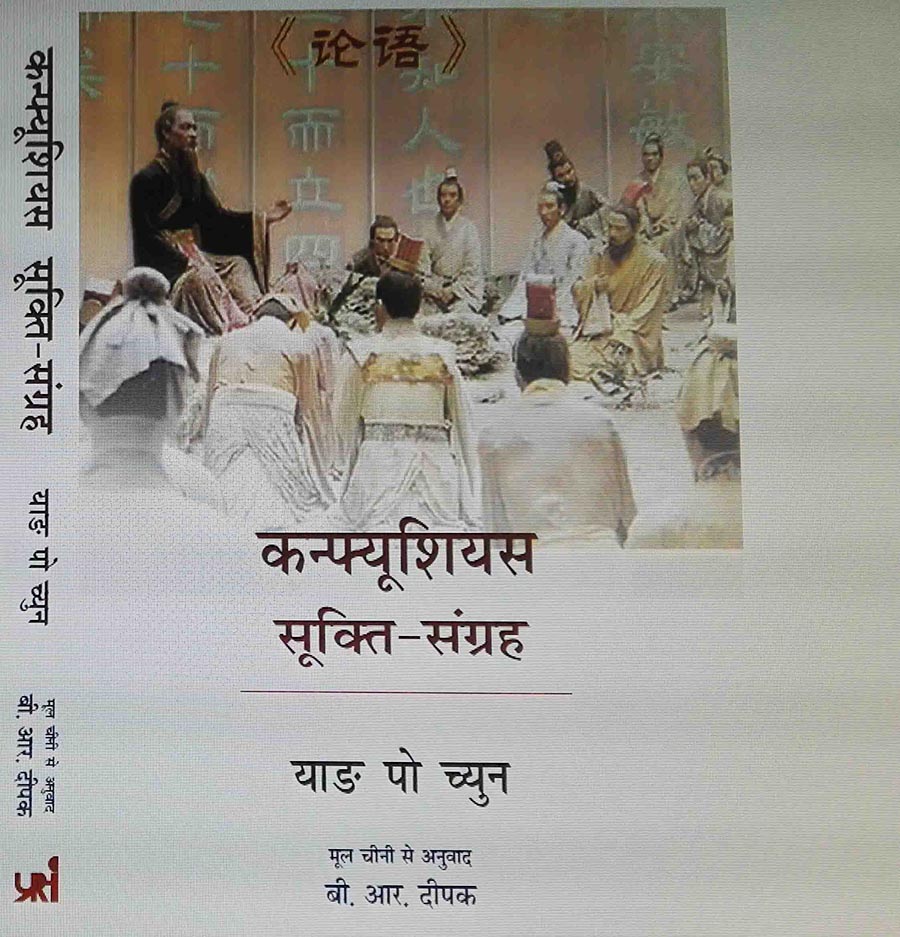
狄伯杰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特别感兴趣,也是第一位将中国历代诗词代表作翻译成印地语的印度人。2009年,他出版了译作《中国诗歌》,其中将春秋战国至元朝的88首中国诗词翻译成了简洁流畅的现代诗歌。狄伯杰对于中国古典作品有着准确而深刻的理解,他不光认为“《离骚》的语言非常漂亮,晚唐的诗开始有了词的味道”,他还看到了先秦散文里强烈的民本思想,“这些作品代表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内涵广大。这就是中国文明和文化的镜子。”
狄伯杰认为中印出版界之间的互动合作一直以来都被忽略了。自马士曼翻译《论语》前九章以后,印度并没有人把此类著作继续翻译成印地语。狄伯杰在十多年前就开始翻译儒家经典《四书》。翻译进度并不快,因为两个国家的传统和文化差异很大,而且翻译对象是文言文,很多中国人读起来都非常吃力。但得益于在中国访学期间的“古代汉语”课程,再借助字典、网络以及各类外文版和注释版,狄伯杰最先“磨”出了印地语版的《论语》。
幸运的是,中印两国于2013年由高层推动启动了“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狄伯杰担任印方负责人,参与审定中国著作书目,他的《四书》系列正好被列入其中。此外,书目中还有24本从未以印地语面貌出现过的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例如《红楼梦》和《白鹿原》。目前,《四书》《骆驼祥子》《活着》《看上去很美》等印地语定稿已经送交出版社,正式出版指日可待。
狄伯杰的不少印度学生对中国唐宋文化感兴趣,但汉语水平和深层次理解还很有限。即便如此,狄伯杰仍然认为在印度传播中国古典文化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是中国文明的基因,如果印度人能够接触到,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促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
